 第十章 生命冊
第十章 生命冊
 第十章 生命冊
第十章 生命冊
。還有的人說,下邊是一人多粗的泉眼,一直通到東海,人一下去,就被吸進去了。這種說法,就像課本上讀到的知識一樣,我曾經對它深信不疑。可隨著時間的推移,在我一天天老去的時候,我對一些問題產生了新的看法。我要說的是:在這個世界上,幾乎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。
在很多時間裡,望月潭就像是童年裡的夢,給人以神性翅膀的夢。它周圍是一望無際的蘆葦,一走進望月潭,那風是濕的,空氣里瀰漫著一點點泛青氣的腥甜。晨光里,水面飄浮著一層鋼藍色的霧氣,往下看,那藍是一層一層的,由淺到深,就像是一幅油畫。每當夕陽西下時,風吹著搖曳的蘆花,蘆葦盪里常常有鳥兒飛出來。蘆花是金色的。鳥是金色的。蜻蜓也是金色的。夢幻一般的金色。陽光照耀在水面上,那潭裡像是亮著一潭洇洇的紅血,每當蜻蜓點水時,就像是浴火重生每年,一到割葦子的時候,潭裡浪花飛濺,還會冒出一人多高的水柱。就有人說,這潭裡有大魚。那魚是吃過人的。於是,幾乎無梁村所有的孩子都被告知:那潭深不可測,有淹死鬼,千萬不要去那裡游泳。可還是有膽大的去了,春才就是其中的一個。
據我所知,每到夏天,春才常常一個人到潭裡去游泳。他每每游過幾圈後,就靜靜地躺在水面上,四肢攤開,隨著波紋漂動,就像是一條大魚。
後來,村里也常有人說,春才是魚托生的。
春才比我大七歲,在我十一歲那一年,他剛好十八歲。十八歲的春才雙眼皮,濃眉,大眼睛,高鼻樑,一米八的個頭,秀美壯碩,一臉紅潤。這麼說吧,他就像是長在田野里的一株挺拔俊美的高粱棵子,是無梁村最帥氣的一個小伙。
但如此壯碩的一個男子,卻是一個悶葫蘆。在我的記憶里,他很少說話。即使他娘叫他,也至多是嗯一聲。在更多的時候,他的聲音大多是由他的手來完成的。他的手比所有人的手都靈巧、快捷。那不是手,那幾乎就是「神的使者」。他的手太會「說話」了。他的手指就像是一把精美的梳子,對女人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。他編席的時候,那席篾子就像是琴鍵一樣,在他手下有節奏地舞蹈著、跳躍著,一格一格地往前推移,詩一樣地律動,倏爾就成了片、成了形了他編的炕席,他編的三層樓、雙扇門的蟈蟈籠子,甚至於經他手編的細葦草圓蒲團,還有裝饃饃的席簍,都讓無梁所有的女人羞愧不已。
有那麼一陣子,方圓百里所有要結婚的姑娘都為能求到春才編的紅炕席而自豪。他能在席上編出「福、祿、壽」等各種圖案,他甚至能在席上編出奔騰的駿馬和叫春的喜鵲因此,「春才的席」在無梁村是一種質量的象徵,是縣供銷社免檢的。這話是縣供銷社派來收席的老魏說的。在設在大隊部的「收席點」里,老魏常說的一句話是:看看人家春才編的席!那時候,村里最讓女人們眼熱和嫉妒的,就是春才了。在女人的嘴裡,春才就是無梁村的一個標尺,男人的標尺。一看見他,女人們的目光里就會開出花來。
在無梁村,老姑父對春才的偏愛是盡人皆知的。春才十八歲時,老姑父就讓他當了大隊團支書。因為他人孤僻,不愛講話,老姑父就把他叫去,做了許多思想工作。後來看他實在是個悶葫蘆,問三句才「嗯」一聲,就又讓他改任民兵連長。可民兵訓練時,他不喊操,喊不出來可老姑父還是喜歡他,就再次讓他當收席站的站長。
有那麼一段時間,夏日裡,老姑父的三女兒蔡葦香時常拽著她二姐蔡葦秀的衣角,站在村口處往北邊看。這時候,剛遊了水的春才會騰騰騰地走回來,他赤著雙腳,穿條短褲,紅堂堂的脊樑上亮著一身晶瑩的水珠,走在黃昏的落日裡,就像是活動著的古銅色的男人雕塑。她們和他,也就是相互看一眼,誰也沒有說什麼。
那時候,按上級的要求,每個村都要配「赤腳醫生」。老姑父的二女兒蔡葦秀,初中畢業後經公社批准當上了村裡的「赤腳醫生」。蔡葦秀性格內向,也不大愛說話。但她是老姑父的女兒,心裡還是有一點傲氣的。她在縣裡總共培訓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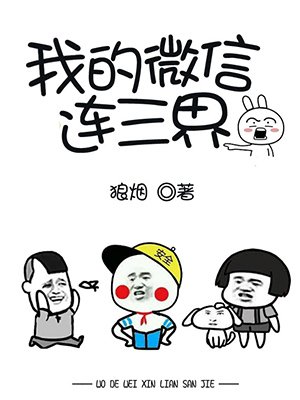 我的微信連三界 本是普通大學生的林海,在微信更新後,被拉入了天庭的朋友圈,從此生活變得多姿多彩。王母娘娘的面膜用完了?拿10個蟠桃來換,不講價。太上老君想抽軟中華?十顆天地造化丹,概不賒賬。紅孩兒想喝哇哈哈?
我的微信連三界 本是普通大學生的林海,在微信更新後,被拉入了天庭的朋友圈,從此生活變得多姿多彩。王母娘娘的面膜用完了?拿10個蟠桃來換,不講價。太上老君想抽軟中華?十顆天地造化丹,概不賒賬。紅孩兒想喝哇哈哈? 危情婚愛,總裁寵妻如命暫時無小說簡介
危情婚愛,總裁寵妻如命暫時無小說簡介 重生九零蜜時光 重生軍長掌中寶,身嬌體軟易推倒。身懷空間有靈泉,虐渣治家樣樣好!上輩子受白蓮花迫害,渣男欺騙利用,一世悽慘痛苦。姜小輕發誓,這輩子要用自己的雙手,為家人,為自己,編織出一個錦繡人生!白蓮花想誣
重生九零蜜時光 重生軍長掌中寶,身嬌體軟易推倒。身懷空間有靈泉,虐渣治家樣樣好!上輩子受白蓮花迫害,渣男欺騙利用,一世悽慘痛苦。姜小輕發誓,這輩子要用自己的雙手,為家人,為自己,編織出一個錦繡人生!白蓮花想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