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第一卷 第2章 通房 被嫡姐逼做通房後
第一卷 第2章 通房 被嫡姐逼做通房後
 第一卷 第2章 通房 被嫡姐逼做通房後
第一卷 第2章 通房 被嫡姐逼做通房後
琴瑟院的大丫頭翠珠端了一個托盤進來,那上面放著一隻青花釉面的茶壺,薛玉容起身,用帕子墊著茶壺的把手,把茶壺拎了起來,往玉姣手中的空茶盞之中倒去。
滾燙的茶水,就這樣裝滿了茶盞。
燙得玉姣的白皙細嫩的手指,生疼生疼的,但玉姣不敢鬆手她知道,只要自己一鬆手,這壺茶水,指不定就灑到自己身上何處了。
茶盞中的水滿了,薛玉容微微一頓。
玉姣如獲大赦,正要長鬆一口氣,薛玉容的手微微一動,茶壺傾斜,滾燙的水溢出茶盞,燙得玉姣又哆嗦了一下。
薛玉容睥了玉姣一眼,淡淡地說道:「端穩了!」
玉姣都要疼得哭出聲來,但還是忍著疼站穩了身體,她知道,自己若是這個時候弄灑了茶水,等待她的,絕對是千倍百倍的折磨。
好在薛玉容沒有繼續倒茶了。
她興致闌珊地看著眼前卑微的玉姣,語氣不屑:「我今日賞你,是為了提醒你,哪怕你爬了主君的床,你在這我依舊是個下賤的奴才。」
「你是賤奴,你小娘是賤奴,你姐姐弟弟,都是賤奴。你莫要覺得,今日侍寢承恩,以後就高人一等了,想著從我的手上翻出花來!」薛玉容繼續說道。
玉姣垂眸,手上的疼不算疼,心中的疼才算是疼。
可憑什麼?
憑什麼他們是奴才?憑什麼薛玉容就是高高在上的嫡小姐?
她也曾經想過掙脫命運,嫁到清白人家去做妻可惜,薛玉容輕飄飄一句話,就從父親那討了她過來。
可她要就這麼認命了嗎?
她偏不!
薛玉容看著站在那,苦苦支撐的玉姣,這才覺得心中的惡氣出了一半兒。
若不是她這身子不爭氣!何苦找這個賤婢生的賤人,來府上侍奉自己的夫君?
薛玉容正要開口,再把自己剩下的惡氣出了。
守在門外的丫鬟翠珠,就開口喚了一聲:「主君,您來了。」
薛玉容聽了這聲音,把茶壺遞給旁邊的趙嬤嬤,自己則是退到了軟榻上,主君進來的時候,她的身上哪裡還有剛才的刻薄氣質?又一次變成了溫婉賢良的世家大娘子。
一道暗青色的身影,自玉姣的身旁路過,玉姣嗅到了那股子松木香,忍不住想到不久之前發生的荒唐事,人有些侷促。
蕭寧遠走到了薛玉容的跟前,看著薛玉容,聲音溫沉地問了一句:「我剛從母親那回來,聽聞你今日身體不適,特意來瞧瞧你。」
薛玉容緩緩起身,溫聲道:「就是昨夜起風,主君不在身邊,我睡得不太踏實,才著了涼。」
蕭寧遠昨日宿在了白側夫人那,他聽了這話,眼神之中似有些許憐惜之意,溫聲道:「晚些我回來陪你。」
薛玉容頓時歡喜起來:「那晚上,我讓人給夫君溫水沐浴。」
蕭寧遠點了點頭,他還有事情要做,於是就起身往外走,這一走,就瞧見了,站在門邊上當門神的玉姣。
玉姣能明顯感覺到,男人的目光在她的身上,微微流連一下,她有些奇怪,男人不久之前,明明醉得一塌糊塗,薛玉容還叫人在那酒中放了助興的補藥,按說男人這會兒,應該還混沌著才是,可這會兒,他一雙眸子漆黑銳利,哪裡還有醉酒的樣子?
蕭寧遠漫不經心地開口了:「這就是今天那個丫頭?」
薛玉容知道蕭寧遠問的是什麼,她的手暗自抓緊了些許,便笑著開口:「是,主君用著可還滿意?」
蕭寧遠的語氣,叫人聽不出喜怒,不回答薛玉容的問題,只淡淡地說了一句:「既是你的人,那就給個通房的名分吧。」
他焉能不知,嫡妻是如何用盡心思,把人送到他床上的?
按說,這種膽敢算計他的人,打發了便是。
但瞧見她怯怯地站在那,如同一隻落水的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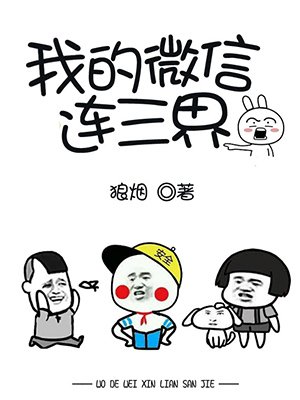 我的微信連三界 本是普通大學生的林海,在微信更新後,被拉入了天庭的朋友圈,從此生活變得多姿多彩。王母娘娘的面膜用完了?拿10個蟠桃來換,不講價。太上老君想抽軟中華?十顆天地造化丹,概不賒賬。紅孩兒想喝哇哈哈?
我的微信連三界 本是普通大學生的林海,在微信更新後,被拉入了天庭的朋友圈,從此生活變得多姿多彩。王母娘娘的面膜用完了?拿10個蟠桃來換,不講價。太上老君想抽軟中華?十顆天地造化丹,概不賒賬。紅孩兒想喝哇哈哈? 斗羅之諸天抽獎系統 穿越到了斗羅大陸,成為了敢呵斥封號斗羅的「絕世強者」聖魂村傑克爺爺的孫子。嗯……這個開局很不錯,但是祖上三代,都是覺醒的鐮刀or木棍武魂的普通人,這可咋整?好吧,血統不夠,金手指來湊!在武魂覺
斗羅之諸天抽獎系統 穿越到了斗羅大陸,成為了敢呵斥封號斗羅的「絕世強者」聖魂村傑克爺爺的孫子。嗯……這個開局很不錯,但是祖上三代,都是覺醒的鐮刀or木棍武魂的普通人,這可咋整?好吧,血統不夠,金手指來湊!在武魂覺 大國重工 冶金裝備、礦山裝備、電力裝備、海工裝備……一個泱泱大國,不能沒有自己的重型裝備工業。 國家重大裝備辦處長馮嘯辰穿越到了1980年,看他如何與同代人一道,用汗水和智慧,鑄就大國重工
大國重工 冶金裝備、礦山裝備、電力裝備、海工裝備……一個泱泱大國,不能沒有自己的重型裝備工業。 國家重大裝備辦處長馮嘯辰穿越到了1980年,看他如何與同代人一道,用汗水和智慧,鑄就大國重工